您好,小编今天为大家分享:【上海南京路的气味与情感地图】或许许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让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来自爱丁堡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讨中心访问学者讲者黄雪蕾,在2022年12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校级学术讲座上的分享,包含讲座及互动内容。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春田掌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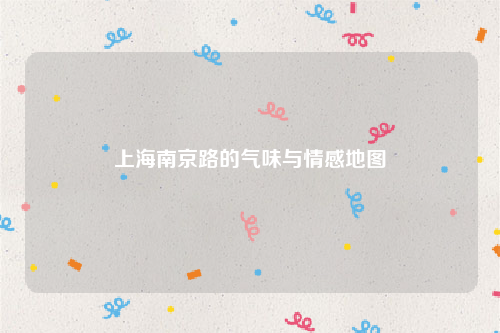
2022年3月,上海南京路。高征图
气味十分重要,它不只仅简略的化学反应和神经反射进程,其背面蕴含着许多价值和含义。
我原先是做电影史的,将近十年前对感官气味研讨发生爱好。新世纪以来,感官研讨在国际上方兴未已,一初步首要由人类学家主张,之后触及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当然,这跟整个大的研讨布景,对身体的关注、情感转向等,都有着深入相关。
南京路如同可被了解为中国现代性的切片。它是上海开埠后,英国侨胞在1840时代最早构筑的马路之一,日后开展成整个公共租界的轴心。它基本上是殖民现代性的物质标志,包含了消费主义、现代技能、卫生次序、中产阶级、世界主义、阶级差序等等。1949年后,它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改革敞开之后,它又成为消费文明的标志,成为旅行地标。
由于杂乱的前史和地标价值,可以将它视作一个地舆文明文原本调查。
KevinLynch是城市规划和文明地舆学方面的专家。他以为,在城市规划中,一座城市十分重要的是thementalimage。咱们对城市的知道,不只仅方位地势,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图画。这个精神图画(mentalimage),是直接的感官知道,加上记忆和前史阅历的叠加构成的。他评论城市,用了制作认知和情感的地图(cognitiveandaffectivemapping)的概念。后来这个词被文学史研讨者运用,从地舆学拓宽到社会政治和文明领域。
KevinLynch的书里以为,mentalimage首要由三部分组成,identity、structureandmeaning,人的感官感知,也是形塑一切这些要素的重要前言。从这个结构动身,我的研讨截取了一个长时刻段中的三个片段,来看南京路的气味和情感地图的改变。
1850时代是形塑南京路identity的重要阶段。就感官而言,“祛味”(deodorization)是杰出特色。随后一个世纪,南京路的空间结构和含义日趋杂乱。到了1930时代,南京路最重要的精神图画,跟物质主义和奢侈相关。到了1950、1960时代,我想着重的是,“再祛味”(Re-deodorization)的操作是如何进行的。
先来看1850时代形塑的嗅觉形象。评论这个问题,有必要把它放到全球史布景中。19世纪后半叶,跟着工业革新和本钱主义开展,西方的大都会,比方伦敦、巴黎等,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纷繁初步大规模城市改造工程。KevinLynch在书里说到,现代城市规划中,都市空间的可读性是个重要考量,嗅觉无疑也被调集去读解空间,去形塑空间的可读性。
另一个重要布景是鼓起于1840时代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这跟工业革新导致的环境恶化休戚相关。英国的议会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可以说是榜首次以准则和法令的办法办理卫生业务,把卫生问题放到了公共领域。其时盛行理论以为,臭气、瘴气会引发疾病,因而“祛味”在公共卫生办理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也是普遍以为的现代气味革新的初步之一。
还有殖民言语中的感官等级次序。其时的西方人行记作品中,印度、非洲等殖民地和公民都被打上脏臭标签。关于中国“Chinastinks”的论说也不乏其人。
总归,在这几个归纳要素效果下,英国侨胞来到上海初步建造南京路时,有意无意把“祛味”作为打造城市空间的重要方针。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方针的,对南京路的metalimage发生怎样的影响?
在实践政策和操作层面之外,我想首要着重隐形的,对时刻、身体和记忆的控制。
来看1856年7月2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一段记载。它是有关南京路粪秽和气味办理的榜首则我能找到的记载。一位殖民官员被指使在早上6:00-8:00,驻守一艘船在福记码头。ParkLane是南京路的前身,街上一切住户,有必要在这个时刻点把“filth”(基本是指粪秽)倒到这艘船上。为确保施行这一办法,他们还派了一名“苦力”监督,并且是佩带徽章的。
这儿可以看到殖民现代性办理的一些典型要素。这次会议记载,不只说明晰粪秽在殖民卫生办理中的重要性,也可看到现代性中的时刻感与身体感的再刻画。
整个工部局会议记载重复说到中国人太不恪守时刻次序。叶文心教授研讨民国上海企业文明时,着重了海关大钟的含义,这一机械设备设定了一个公共时刻,将其内化到城市日子和市民感知中。这个比方中,南京路的气味地图与时刻感被人为勾连起来,形塑了南京路这一共同的identity。其时对华人社会来说,南京路的办理跟华人市政办理构成明显差异,《申报》等中文报纸上有许多评论。此外,感官感触会成为记忆,层层累加,变成城市精神图画的一部分。
再举个小比方。1938年的《字林西报》上,刊登了名叫Stinky的读者来信,是一位法国人,他诉苦早上上班路上,总跟粪车宣布的冲鼻臭味相遇。他主张,法租界当局应该分发一些法国香水,比方Lentheric这个品牌1930时代开宣布的名为“上海”的香水。他又恶作剧说,调香师的创意必定不是早晨八点的上海领事馆路的滋味。
这样的前史文本,带领咱们去幻想这座城市的气味。城市的气味又与化妆品工业和香水的物质文明勾连起来,对文明记忆的形塑,起了十分要害的效果。
再看一个比较具体的气味办理的操作手法。其时办理气味,尤其在上海,重要的手法是填平沟壑。上海地处江南水乡,天然地貌水沟纵横。在其时的农业出产、交通运输和日常日子中,水沟发挥了巨大效果。但在西方公共卫生理论中,水,尤其是死水臭水,被视为天敌,加上新的出产和交通办法、经济开展办法的引进,上海的水沟在19世纪后半期被许多填埋。即便十分小的坑洼,也被以为是繁殖臭气污染的温床。前期工部局会议录中,有许多记载评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技能手法是建筑下水道。巴黎和伦敦的下水道,成为19世纪西方现代性的化身,上海的下水道建筑简直同期打开。1860年左右,其时英国侨胞已初步建筑下水道网络。南京路是网络上的重要轴线。下水道在文学幻想和感官文明史上都有重大含义。将污秽驱逐出视觉、嗅觉的感官场域,也是西方现代性的成功主义的物理标志。这一提高现代都市可读性的进程,也意味着生态的人为重构和感官感触的再分配。并且,这样的重构和再分配往往是权利不对等的产品。
1930时代是上海摩登的巅峰。这座半殖民地东方大都市的精神图画,与物质主义、世界主义和奢侈颓丧严密相连,留存到今天的“魔都”形象。
气味在其间发挥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可以来看一部文学作品,刘呐鸥的短篇小说《礼仪和卫生》,发表于1930时代,是典型的新感觉派小说。作者描画了南京路大街的三种空间类型,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气味和感官感触。
先看榜首种空间类型。它是现代办公楼,首要会集在南京路挨近外滩的当地。男主人公启明是一位律师,在写字楼上班。他替一位太太打赢离婚官司后,在阔太太中忽然变得炙手可热,办公室里每天都有绸缎的冲突声和香水胭脂的气味。
接下来一段,更详细地描绘了这样一个春日下午:
这是典型的新感觉派的描绘,着重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的归纳体会,令男主人公愿望蠢动。现代办公空间里的气味和感官感触,其他新感觉派作品中也常呈现。比方,穆时英的《烟》里描绘男主人公的办公室:
穆时英的短篇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中有一段,讲一位医师的感官体会:
南京路上的写字楼,连续了1850时代以来的祛味理念。另一方面,这些空间也是对女人敞开的,因而变成了一个愿望公共化的场所。感官,尤其是嗅觉,是重要的中介,其间也触及性别本钱的沟通,某种含义上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差序。
让咱们再回到《礼仪和卫生》。律师启明在办公室被挑动起愿望之后,决议提前下班,下楼来到南京路上。这一段调集了各种感官感触:
当他来到药房时,呈现这样一段对话:
这段描绘怎样解读?南京路的大街空间里,咱们看到的是世界主义的感官和权利游戏,也是半殖民地的实际图景。洋太太带着花香和青草的气味。低了一等的斯拉夫女,则发出野味的气味,更挑动愿望。对黄种人启明来说,他享用这种含糊的愿望投射。嗅觉是一种既密切又隐秘的前言,但真实满意愿望的方针,要去别处寻觅。
他去哪里寻觅愿望的完成呢?——是离南京路不太远的一条胡同。这儿又有一段描绘:
这儿充分体现了分解的种族-空间结构。胡同里市民日子的空间,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或南京路街区的精神图画的组成部分。风趣的是,启明的感官感触,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上海胡同蒙上一层异国情调。作为一名高级华人,他选用了西方人的视角。至于满意自身身体愿望的具体方针,他挑选的是一位中国的妓女。所以,半殖民地世界的割裂感也包含身心的割裂,而感官是折射意识形态的介质。
终究来看上世纪五六十时代,南京路的气味地图是如何被重塑的。这个文本以南京路为布景,叫《霓虹灯下的岗兵》,是1962年首演的舞台剧,1964年改编成电影。
作品缘起是1959年初步的“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是参加解放上海的一支连队,被派驻到南京路。将好八连列为标兵,与南京路的标志含义有关。只要抵挡住本钱主义的糖衣炮弹和香风害草,社会主义才能够站稳脚跟。南京路的奢侈感官空间,有必要被赋予新的含义。
风趣的是,刘呐鸥作品中的三种空间类型,也呈现在《霓虹灯下的岗兵》中,气味相同是传达意识形态的前言。
最初几位反面人物进场的空间,相似启明的现代办公楼。两个美国人支撑的国民党特务走进这栋楼,说了这句台词:“让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咱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台词充满了感官上的影响性。南京路的香气,与霉味、腐味构成明显对照。写字楼空间标志旧的次序。新与旧的对决也是香与臭的对决。
整出戏的剧情首要发生在南京路的大街上。第二场开幕是这样的画面:
剧照上可以感触到大街上香水胭脂的气味。这儿有先施公司的橱窗,还有穿戴旗袍的女士。
下一幕,一位叫做赵大大的解放军兵士在南京路巡查,遇到一个卖花女叫做阿香。
阿香问赵大大说,夜来香要吧。赵大大赶忙躲开,阿香仍是捉住不放。赵大大则持续背身。阿香着重说,花是香花,你看看,白兰花、栀子花、茉莉花、玳玳花,还有夜来香。随意捡一枝回去,放在房间里,到夜里确保特别的香,你太太必定会喜欢。赵大大手足无措,持续用言语着重,小大姐请你站得远一点,好不好?阿香说,那好吧,我不要你钱,你就去闻一闻,然后把花送到赵大大面前。赵大大持续逃避,把鼻子捂起来。
这段话让咱们联想到刘呐鸥笔下南京路的春日。但跟启明不同,赵大大把感官影响和愿望剥离了开来。他把愿望放在牺牲共产主义的精神寻求中,这当然是该剧的中心思维。风趣的是,也十分契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编剧还组织了一位不坚决的兵士陈喜。陈喜也是好八连的一位兵士,在南京路上被乱用渐欲迷人眼。这时他的爱人从老家过来,她十分热切地望着陈喜,而陈喜眼光中如同有一些为难的表情。后来的对话显现,陈喜嫌她穿的衣服太土。
由于陈喜十分享用南京路的香气,就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
终究,陈喜这个反面教材,被转化成坚决的共产主义兵士。教育功用也在感官转化进程中显示。香风一词,后来成为上世纪六七十时代政治盛行语,资产阶级的香风毒气,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这些政治上的惯用语,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再看一个空间,是南京路周边的胡同。这儿又有一段卖花女阿香跟赵大大的戏。阿香因无力归还欠债而遭受暴打,将被贩卖到香港。赵大大呈现解救了阿香,还给她还账的钱,令她感激涕零。这个胡同大致应该是启明买春的街区,启明的故事里,它是半殖民主义缝隙中的情色空间,是满意小资产阶级个人愿望的场所。但在《霓虹灯下的岗兵》中,相同的胡同空间,意涵更为单一。它是以南京路为代表的殖民现代性的敌对面,是劳苦大众受压迫的标志性空间。
赵大大扮演的不是寻乐者,而是救赎者。他呼吸着劳动公民的气味,满意的是笼统的团体和国族的愿望。把这个场景跟前面的卖花场景放在一起,大家更可以体会到,愿望与感官是如何被剥离的。
有关胡同空间,还有第六场的棚户区。依据剧本描绘,它离南京路不太远。苏州河边上,其时有许多棚户区。电影画面中,咱们似乎闻到湿润污秽的气味。剧本还说到馄饨的香气和五香茶叶蛋的滋味,阿香的母亲去点香求菩萨保佑女儿不要被拐卖到香港。当然,菩萨没有帮助到他们,终究是解放军解救了阿香。在这儿,城市的精神图画被二元化。棚户区和胡同,是赤贫、迷信和失望的化身,而馄饨和茶叶蛋的香气是公民的感官指涉,他们等候救赎。
来看一处十分有意思的结尾,是在红玫瑰和白玫瑰的香氛中做结。这幕戏发生在南京路的花店,特务和解放军别离买了一束白玫瑰、一束红玫瑰。接下来场景发生在咖啡馆,咖啡馆的滋味是殖民现代性的化身。但终究,南京路花店的滋味和咖啡馆的意涵都被翻转,变成了敌我奋斗的道具。特务在白玫瑰中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被手持红玫瑰的解放军识破。红玫瑰战胜了白玫瑰,从颜色符号学上,也标志了共产主义的成功。
由此,可以看到南京路的气味地图得以重塑,一切新的含义都建立在旧的含义的基础上。所以,一座城市的精神图画,是在感官感触中层层累加,与前史严密相连。
我简略陈述到这。终究想以2022年末的南京路作结。人们戴着口罩,也或许嗅觉失灵。你闻到的南京路是什么样的气味,跟当下的前史又怎样勾连呢?它必定会化作咱们个别和团体记忆的一部分。
发问:气味分许多种,不仅仅香和臭,背面的谱系,牵扯到心思机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个人阅历,比方闻到气味发生心情改变,导向什么样的研讨。有没有一些感官史入门的书本,或是研讨办法导向性的理论作品?
答:香和臭中心有着宽广的谱系,但现在大都气味研讨的书,要点聚集在香臭南北极。尤其是除臭。一本十分重要的书,是法国前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Corbin)的《瘴气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幻想》(TheFoulandtheFragrance:OdorandtheFrenchSocialImagination),可说是嗅觉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书里写的除臭与现代性,变成了干流的研讨取径。
关于香和臭中心,纤细的个人阅历和感触,引发的心情和心思机制,十分值得做感官研讨的去探究。人对气味的感触,有很大的含糊空间,也被现代科学所印证。相同的化学分子,在不同情境中闻,会闻到不一样的气味。科学家以为,人的大脑,视觉处理机制有比较明晰的形式,但嗅觉对应形式不明显,不是“一便是一”。闻到某个滋味,觉得是香是臭,有许多阐释空间。
对于香和臭南北极化的主意的反思,也跟当下后结构主义有关。咱们企图从头建构一个并不是被启蒙主义的二元分解、理性和理性这种图谱决议的视界。关于感官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切入的言语。人的个别阅历,包含正阅历的疫情等,每一个人的感官感触、身体感触,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改变,无法用二元敌对的办法规约。
至于感官史入门的教科书,DavidHowes,康斯坦丝•克拉森(ConstanceClassen)编了许多书。两位加拿大人类学家编的书不只包括人类学领域。2018年,DavidHowes编了一套四卷本的感官研讨丛书(SensesandSensation:CriticalandPrimarySources)。2014年克拉森编了关于感官史的六卷本ACulturalHistoryoftheSenses,是通史性的丛书——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今世,但要点限制在西方。这两套丛书中触及的非西方的研讨都很少。。
发问:其时景象史的研讨,着重人对景象的认知和再形塑,也更着重视觉。这是对前面研讨的反思和打破吗?别的,感官史和景象史的联系,不知是怎样的。
答:你说到,景象史着重人对感官的再形塑,人类学家前期引进感官研讨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与其十分挨近。便是说,感官曩昔如同仅仅科学家研讨的领域,现在着重感官是文明和社会去形塑的,他们喜欢用的词,是“culturallyandsociallyconstructed”。
这个观点今天并不稀罕。我想着重,某种程度上应跨过这样一个论说,从头思索景象自身,或感官自身、化学自身:当病毒把你的嗅觉神经破坏,瞬间什么都闻不届时,这种体会对咱们了解文明和社会有什么样的奉献呢?
十年前初步做气味研讨时,我也首要想看咱们的文明社会前史,究竟怎样形塑感官。直到终究快要写完全书时,才有更深一步反思。
近些年人文学术的开展,新物质主义(newmaterialism)、后人类中心主义(posthumanism)等,都是比较前沿的视角。有一个共通点,便是让咱们从人的视点略微往后退一步,企图从动物的、环境的、物的视点,去看这个地球。尤其是2020年今后,疫情及环境问题,给了咱们深入牵动。“人类中心主义”看问题的办法,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刻点。
发问:当咱们从作品中捕捉到这样一些嗅觉元素,可以怎样向“嗅觉”主张正面强攻,相关到一些咱们比较了解的出题?别的,比方三十时代的左翼文学中,其时有没有去抢夺、从头再造嗅觉?
答:古典文学宝库里,有许多值得研讨的资料。2022年10月我在台湾的中央大学明清文学研讨所做了一个讲演,其时讲了红楼梦。我不是专门从事明清研讨的学者,沟通时听到不少有意思的反应,从明清文学或更前期文学,都可以从头思索中国传统的感官视角。
怎样就嗅觉谈嗅觉。我想说的是,不谈外围,是不或许的。气味不只仅感官的问题,它总是相关许多的含义和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嗅觉谈嗅觉,我想到科学和人文跨界的取径。两年前,哈佛大学出书社出书了一本书叫做Smellosophy。作者是一位科学史研讨者,她的办法是采访许多科学家,写了相似嗅觉的科普读本。一个启示是,可以从神经元和分子的视点寻觅答案,尽管未必必定能找到。当然,真实操作起来很难。绝大大都人文学者没有科学练习,要评论那些分子式有很大难度。但我读那本书读得着迷,它带领你进入脑神经元,去读解周边的气味环境。
第二个问题,关于左翼文学怎样抢夺、重塑嗅觉,我自己书里有一章处理二十时代的发明社及鲁迅和茅盾。我首要关注的,是这些作品中关于身体和情欲的滋味。
除情色小说之外,古典小说中,对身体和情欲的滋味,往往是概念化的,首要用兰麝一笔带过。到了二十时代,有个很重要的转向,对身体的描绘初步选用一种科学的、脚踏实地的视角。
比方,闻到一个女人的香味,张资平会说,闻到一种弱醇性的呼吸的气味,而不再是兰麝了。这儿透射出很重要的近代身体观和感官文明的改变。
前两年复旦大学康凌教师的作品《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新文艺的身体技能》,评论了诗篇中的身体技艺,是从声响的视点处理的,从诗篇带来的声响感中,评论诗篇怎样与身体相关,是研讨革新的一种不同取径。左翼文学中,我相信必定也有许多跟气味相关的,又是一个值得研讨的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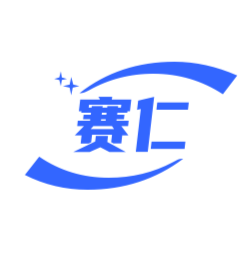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