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升一把抱住程木滨,脑袋死劲儿磕脑袋,道是:“天爷爷地奶奶,恁可想死俺咧哥们儿。”程木滨眼窝里涌出了泪珠,刘东升掐着发小的双肩哈哈笑。
待问清来由去向,刘东升也不多说,拉起程木滨的胳膊一起去吃早饭。吹一声口哨,挥一下手,叫上了路边两个小乞丐。拐两道弯,来到一处街角小食摊前。早前他们要饭那会儿,全城也就八九个个体早餐摊,这个离车站最近的小食摊,是小时候两人乞讨时经常混吃喝的地儿。摊主大叔心眼儿好,俩人没少在这里吃白食。

墙角找个背风地脚坐下,刘东升给每人各要了一碗甜沫跟老豆腐,外加两个窝头。黑糊糊的一张小桌子上瞬时被吃食排满,他馋家乡的美食久矣,甩开腮帮子开吃。程木滨心里堵,吃半个窝头喝一碗老豆腐,便不再吃东西。不见了小时候的鼻涕邋遢,看着刘东升又长些肉的大黑脸,程木滨把这几年家里发生的事简要说了说。猛然听到师傅去世,刘东升手里的窝头滑落到桌上。没想到,管咧三年多饱饭的师傅再也见不到咧。
半晌,回过神儿来,刘东升推开眼前的饭碗也不吃了,说道:“jiè(这)次回来有俩事。一个是要找些人去深圳做建筑工,木滨,恁弄摸前儿(现在)在家里呆不下qì(去)咧,zhòu(就)一块儿去ban(吧),俺在那边儿蹚出咧门路,咱一块儿挣大钱。”
程木滨说:“恁挣钱俺、俺信,可俺不能去建、建筑工地,忒危险,俺jiè(这)条命儿是俺、俺们家四代独苗儿,俺得好、好好活着派、派大用场。”
刘东升道:“再个事,俺要在爸爸的坟前立碑,他老人家一辈子罗锅儿腰人前抬不起头,娘球的,俺得让他在地下有颜面。”
程木滨说:“干脆连、连恁爷爷的碑也、也立了咧ban(吧),他可、可是咱村儿里砍杀过日、日本鬼子的。”
一说到爷爷,刘东升不再言语。本家五服叔叔讲过,爷爷在村子里是有争论的,被人说成是汉奸,说成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爸爸就是因爷爷的这个名声才上吊去世的。
说话间两个小乞丐风卷残云,把桌上的吃食消灭殆尽。起身,刘东升把十块钱递给摊主,摆手不让大叔再找钱。吃饭付双倍多的饭钱,摊主没认出两个长成小伙子的当年小乞丐,看着刘东升一时懵头。“恁给钱抛得高,就像张飞战马超”,“恁给钱扔得矮,好像八仙来过海”,两个小乞丐冲刘东升弯腰点个头,唱着他们曾经的要饭歌撒欢儿跑开了。
也不商量,刘东升拉起程木滨走进不远处两层红砖楼的国营铁佛百货商店。百货商店就在离火车站两百多米远的东南方,打小儿在站前要饭,俩人却从没有进去过。从袜子、鞋子、裤子到上衣、围脖跟帽子,刘东升一应俱全地给哥们儿置办了全新的一身。人配衣裳马配鞍,看着穿上新衣裳的程木滨倒也相貌堂堂,刘东升想怪不得师妹能看上他看不上自己,还真不好比。买完衣服,又到红日照相馆,兄弟俩拍了平生头一张合影。
刘东升确实挣钱了,在深圳四年多时间里挣了五千多块。坐在照相馆门前的马路牙子上,程木滨让东升说说这几年是咋mu(怎么)样在外面过来的,自己头一回出远门,心里头没底。刘东升暖瓶嘴儿朝下,一股脑儿把几年来在南方工地的经历全都倒了出来。
初去时在工地上当小工,推砖拉车扛水泥。一年四季一身衣服,春夏秋冬吃住在工地上。工地没建之前,睡离地半尺散着潮湿气味儿的草棚子。工地起了框架后,就随意地窝在在建楼哪里睡下,随着工地进度不断地移转腾挪,任它夏天蚊虫叮咬冬日冷风嗖嗖。
发生转机是缘于一次被骗。那是到深圳的第三年,一个新工地挖出上千方土方需要用小车推运到两百米以外的空地上。包工头高额工钱诱惑,刘东升跟四个伙伴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干到晚上腿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咬着牙挺了二十三天,五个人终于将小山似的土推完。去要工钱时,包工头已跟工地结完账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五个人再去找工地干活儿,不论工钱多少只要日结。一座十层的商业楼需要一年内完工,建筑工地急招人就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干了七天后,负责人见几个小伙子能干肯干,为留住他们主动加了工钱。刘东升带着几个人白天绑钢筯网,晚上打混凝土,黑白轴转加快了进度,工地苏队长再给他配两个人成立了混凝土小组。过些日子又加人,混凝土小组在苏队长嘴里在办公室标进度的黑板上,变成了混凝土队。从卸沙石水泥,到搅拌机搅拌,再到推送混凝土和振动夯实,刘东升混凝土队一条龙全活儿。
“肩膀冲前弯下腰哦,背紧纤绳放平脚哦。拉咧一程又一程哦,不怕水急风又高哦”!
干活儿劳累时,他教弟兄们唱家乡运河上传下来的纤夫号子解乏,有时也会唱一唱莲花落,既给大家带来快乐,也是他少有的可以显摆的文化本事。迎着日出送走晚霞,这一支从田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铁军闻着钢筋水泥的气息,近一年里没有走出过工地大门。
刘东升混凝土队对保证工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竣工时苏队长给了他八百块钱奖金。他随手全都扔给了弟兄们。花花绿绿的钞票在空气中散发开来,似弥漫着迷人的芳香。二十几个从乡村怀揣着梦想来特区淘金的年轻人,哄抢着,追闹着。刘东升一战成名,人们知道他来自铁佛城,又有他充满情趣的特色家乡话,就忽略了他的姓名而约定俗成地喊他小铁佛。小铁佛混凝土队队长刘东升,成了深圳各个建筑工地争抢的香饽饽。这次他回来,就是要拉人头扩队伍,回深圳大战江湖,把钱挣个老鼻子。
程木滨大脑袋一动不动,两眼直直地听着,深圳小铁佛的画面电影一样在他眼前一幕幕闪过,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讲既新鲜又有些恐惧。
能说出嘴的是荣耀,不能说出来的是心里头对女人的渴望跟每个年节的孤独。特别是对女人的渴望,贼被狗咬,他实在是难以吐出口来。
夜里,工友们睡觉前最后一件事就是说女人寻乐呵儿。有娶过媳妇的,有谈过女朋友的,都笑他都这么大还没摸过女人的奶子,白活咧。他也觉着自己白活咧,小时候不受女孩子待见,长大咧师妹也瞧不上他,他一次次地想像着触碰上女子的感觉。终于那天瞅着了个机会,女工小萍独自在一个房间里涮涂料,他开玩笑地抓了抓小萍的辫子,见没多大反应,得寸进尺地从身后搂住了女子。浑身燥热涌起,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移到了小萍的前胸上。邪欲在他脑海里耍泼撒赖的时候,小萍丢掉手里的刷子拼命挣脱了,骂了句“流氓”哭着跑开了。
除了对女人的渴望,最难过的是春节。他无家可归,被留下来看守工地。每年都从工头那里借来收录机,到夜里就爬上工地最高层的楼顶,独自一人拿一瓶酒,对着起伏着烟花的天空放歌:“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遍遍地放歌,一遍遍地对天狂喊:“俺想女子,老天爷给俺个女子ban(吧)!”像一匹草原上的孤狼,他在工地上尖叫。一个晚上,他再也按纳不住内心的狂躁,跑进了一家没有关门的发廊,跟一个同样没有回家过年的发廊妹第一次释放了他的盆腔,用钞票交换了女人的肉体。一连五天,白天回去守工地,夜里住发廊。第六天再去时,他被发廊妹拒绝了。连发廊妹也嫌弃咧俺,世上的女人咋都不喜俺呢?刘东升对女人又想又恨……
刘东升回村里找人跟立碑,去看四年多不见的师娘跟释参师傅去咧,为咧再战江湖挣大钱,拉人头扩队伍去咧。拿着发小儿给的二百块钱,程木滨售票厅买了票。进候车厅来到厕所,趁没人注意时每只鞋里分别塞放了四张二十块钱一张五块钱,少许余款放在上衣内兜。而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挤上了南去的火车。
上海是爸爸发迹也是背祸之地,程木滨心里想着不仅挣钱还账,也一定要在那里混出名堂来,像东升这样富贵还乡风光地回来。要让奶奶、爸爸跟师傅地下含笑,要让师娘、香秀跟香秀肚子里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要让村里人瞧得起。尤其是那个没出生的孩子,再也不能让他像自己小时候一样挨饿跟受歧视咧。
“呜”一声长鸣,火车驶离了铁佛城,奔向了遥远而陌生的大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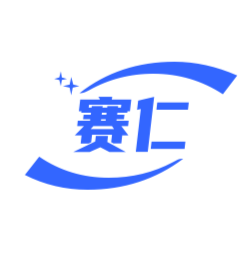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