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都是内心苦闷的天才!因为细腻、敏感、脆弱又不安,所以他们总比常人悲观消极一些。
有人说,所有的结局最后都应该走向毁灭,如果你觉得圆满,那一定是还没有结束!
我其实同意这种观点,但我并不想兜售悲观主义,只想说贾宏声,他真的是一个悲观的艺术家。
他亲手将生命停在43岁,在本该不惑的年纪,从14层楼一跃而下,张开翅膀的瞬间,他才与这个世界和解。
贾宏声出生在吉林一个戏剧世家,父母都是话剧演员,他在1985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同窗的还有巩俐。1987年在校期间,贾宏声就主演了史蜀君导演的《夏日的期待》,开始了演艺事业。1988年又主演了李少红导演的《银蛇谋杀案》。
因为俊朗又略显忧郁的面容,成为那个时代最受追捧、最具偶像潜力的新人。那个时代好像都喜欢沉默寡言、忧郁有才的男子,比如黄磊,比如贾宏声。但贾宏声并不是为讨好观众,故意假模假式的装忧郁,他骨子里的悲伤一直在暗暗作祟。
他开始觉得自己享受走红的样子很做作,很恶心。于是,他踩碎了以前的录像,踢坏眼前的电视机,他说:“92年之前拍了很多戏,脑子都拍空了。”他开始尝试话剧。
1992年,他出演《蜘蛛女之吻》,这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他也第一次在排练场接触到大麻。正是迷惘抑郁的时候,贾宏声和大麻,不知道是谁选择了谁。
到了1994年,他又接触到了摇滚乐,他觉得自己的压抑和暴怒可以倾泄而出。他沉迷于摇滚,更说自己是约翰·列侬的儿子,他积极组建乐队,拼命练琴,嘶吼和咆哮,而那一年,魔岩三杰也在红磡振聋发聩。
摇滚和大麻,让他的性情变得暴戾。他推掉大部分邀约,成天在极度抑郁或者极度愉悦之间往返。
偏激、极端、疯狂和歇斯底里,女友伍宇娟一直陪着他,试图用爱和包容、理解去感化他,但他病了,这病不是光靠安慰就可以迷途知返,最后女友承受不了,无计可施,只能挥泪放弃。
这时,贾宏声的父母也不惜辞掉工作,来北京专心照顾他,期间他甚至向父亲拳脚相加。后来他开始出现幻视、幻听,等一系列精神病症状,于是他不得不停止《日蚀》的拍摄,住进了精神病院,治疗和戒毒。
1997年,控制了病情的他重返荧幕,出演了王小帅的先锋电影《极度寒冷》。他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行为艺术家齐雷。为了和冷酷的社会对抗,他开始了一项行为艺术,立秋土葬、冬日水葬、立春火葬、夏至冰葬。
这部影片,让贾宏声进的太深,出不来。其中“冰葬”的那场,贾宏声坚持要在冰上呆坐足够长的时间,最后身体不支,被送到了医院。贾宏声在拍摄之后,也会坐在显示器一遍遍看回放,不能自拔。这次拍摄也激发了贾宏声一些新的人生追求,那便是纯粹。
1998年,贾宏声拍摄第六代导演娄烨的《苏州河》,认识北漂的周迅,并陷入恋情。这部影片在国际获奖无数,第2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第15届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十佳。
剧中的贾宏声饰演因欺骗感情而救赎的马达,他陷进爱情,又谋杀了爱情,之后他挽回、救赎,最后两人一起在死亡中让爱永存。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么?
-会。
-会一直找下去么?
-会。
-你撒谎。
周迅凭借《苏州河》一跃成了炙手可热的女星,片约不断的她和贾宏声越走越远,之后她与朴树恋爱了。后来周迅曾经打电话给贾宏声,说朴树很像他,长得像,抽烟的样子也像。贾宏声听了觉得挺可怕的,就把电话挂了。
贾宏声在孤独的路上越走越远,他说“拍电影太虚伪,什么都是假的,是骗人的。”于是2001年,他和好友张扬拍摄了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真实的电影《昨天》。
他的父母也以父母的身份,加入到这部电影,这种本色演出,在中国电影史上绝无仅有。也正因为太真实,所以很多黑暗和锋利,赤裸裸的剖析让我们沉重的不能呼吸。
影片中,父母说贾宏声是一个脆弱、虚荣的人。
因为父母从东北过来,总是操着一口大茬子味,所以贾宏声强迫父亲把说了大半辈子的“这事儿咋整”改成普通话:“这事儿该怎么办”;父亲要陪他出门走走,他嫌父亲带来的裤子太丑,丢人,强迫腰围两尺六的父亲提着气穿上自己两尺的牛仔裤;
他痛恨父亲是个酒鬼,他曾质问:你活的有意思吗?你快乐吗?”说罢,更直接扇了父亲两个耳光。
他痛恨自己不是欧洲血统,不是约翰·列侬的儿子,于是他躺在草地上失声痛哭。
影片中的他,被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他却显示了他友好的一面。
在难得的晒太阳时间,他平静的给蚂蚁喂食。
看见垃圾,会弯身丢到垃圾桶
我忽然明白,他对最亲近的人暴戾,不过是在自己身上刻出血迹。他对自己最大的报复,就是不断刺痛周围的人。影片中他说:“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还没扛到头呢!’我没有选择,只能死磕,跟所有的人磕。”
影片的最后,他饰演的自己最终和现实和解,当人们都以为他彻底豁达时,现实中的他却从十四层楼上一跃而下,他彻底自由了。
贾宏声的父母否认儿子因为精神病自杀,他们说:“宏声他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可能是我们谁也给不了他。他去寻找了。让我们静静地帮他走好……作为家人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不同的使命,有的来传播爱,有的来传播恨,有的变风变雨变阳光,有的成疯成魔成暴戾。说到底,都是过客,能留下痕迹,便不枉这一遭!
抑郁也好,找寻也好,贾宏声抱着他未被浸染的理想远走他乡,这是他的归宿,不值得叹羡,但也请给以尊重。
没有毒品的贾宏声不会跳楼,现在——应该活的更好!
“列侬的儿子”
贾宏声:我有没有英国血统?
父母:没有,咱们正统的中国人,我和你妈祖上三代都是四平的。
贾宏声:不,我肯定有英国血统。
父母:为什么?
贾宏声:因为,我是列侬的儿子。
在后来的自传体电影《昨天》中,贾宏声把自己吸毒的经历又演了一遍,其中就有这个片段。他也成为大陆第一个主动公开吸毒史的明星。80年代末90年代初,20出头的贾宏声甚至登上过《大众电影》的封面,那是何等辉煌!
第一次吸大麻,是在话剧《蜘蛛女之吻》的排练期间。在剧中,他扮演一个吸毒者兼同性恋者。当时听说吸点大麻对调节精神和表演很有帮助,正好圈子里有人吸这种东西,大家便撺掇着去找。
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烟雾笼罩。贾宏声抽了之后表情僵硬,忽然冲出门去呕吐,大家问他怎么了,他的头还伸在门外,手却朝屋里的人比划了一个“V”,屋里的人一阵大笑。
这是1992年的事了。在经历了1949年之后狂飙突进般的禁烟运动后,中国内地曾长期处于“无毒”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一些留学生或老外把毒品带了进来。而与外国人接触比较多的音乐圈,尤其是摇滚圈,就成为最早沾染毒品的人群。
吸毒就像传染病一样,终于由摇滚圈子传染出去,其中一根,就传到了贾宏声手里。据贾宏声周围人回忆:“知道他是第一次抽,可是他一抽就没够,他学什么都特别快。那时候流行重金属,他就穿皮夹克,打耳环,扎头巾,他就那样,挺较劲的,做什么都特别过。我记得那天他的反应就特别强烈,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张杨的评价是:“他吸毒其实是早晚的事儿,对他来说那是一种时髦,他身上确实有一种很虚荣的东西。”
这之后,他便无法自拔。据他回忆,“93年,我主演《周末情人》,那个戏是我抽(大麻)最厉害的一段时间,好像只有那样才能找到演戏的感觉。过了一年,我又拍电视剧《梁祝》,那是我第一次演古装戏。整个人都傻了,一点感觉都找不着。导演一喊开机,我就不知怎么演,还得靠抽,整部对我都是晕着演的,太可怕了。演完那个戏,就开始厌恶演戏。”
与贾宏声相恋多年的女友伍宇娟,试图用多种方法帮他戒毒,最终无效,二人分手。
贾宏声也开始陷入绝望中,“像坠入黑暗的深渊”。他发现,毒品对他的精神解脱不起作用了,成了累赘、黑洞。
2010年,他从北京朝阳区的家中一跃而下。身边的人都一再强调,贾宏声离群索居最终自杀,毒品不是主因和诱因,是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与社会格格不入,但《昨天》的导演张杨事后回忆:拍完《昨天》之后,有许多剧本找到贾宏声,不是让他演毒贩,就是坏蛋。从此,贾宏声没有再接演任何电影。短暂地做过话剧,而绝大多数时间他就在家中,甚至手边的电话响起来他也不接。
欲望洞开的丛林时代
就在贾宏声接触大麻的那一年,北京市公安局受理了一批地下乐队的摇滚乐手吸毒案件。当时在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的张明注意到:“这些摇滚乐手全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既有吸毒几十次、长达两年之久的,也有仅吸毒一两次的。摇滚乐队常为外国人演出,那些含有大麻的香烟,就是观看演出的外国人提供的。”
现在回想,80年代的狂飙中不仅有经济自由,还夹杂着很多未来可能遭遇的社会问题,包括毒品。贾宏声沉沦毒品的那段时间,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禁毒工作起步的初期,法规和打击力度都有所欠缺,结果如贾宏声一样的涉毒者们,愈陷愈深。
贾宏声吸毒两年后,娱乐圈的击鼓传花终于传到歌手罗琦手里。
有关罗琦的故事在多年以后的当红选秀节目中再次重温,只是很多细节仍令人不忍耳闻。1997年7月,罗琦在南京机场转机时突然毒瘾发作,神志不清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带她上街买海洛因,直接被司机带到了公安局,尔后被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3个月,这也是内地娱乐圈第一次有艺人吸毒的正式新闻,舆论哗然。
1994年,20岁不到的罗琦开始吸食毒品:“因为心情很不好,就开始慢慢地尝试。当时很多人说这个可以给你很多灵感,但其实绝对是个误导。”几年后罗琦已经无法正常录歌。
罗琦出事后不久,1997年9月,演员朱洁因吸毒过量而死。这位爱新觉罗的后裔,此前刚刚在禁毒片《长大成人》中担任女主角,扮演的是一位吸毒女。结果假戏真做,染上毒瘾,长期吸食大麻,电影还未上映女主角已然离世。朱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据老师说她表演天分很高,又漂亮。她与演员江珊、徐帆、陈小艺等都是同班同学。
毒品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曾将现代毒品史的起点放置于19世纪20年代,并表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起因于皮下注射器的研制和把它们用于治疗神经痛以及慢性病人。在《上瘾五百年》一书中,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指出,“有四项医学发展不但加速了精神刺激革命,也使此一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令人担忧。它们是:吗啡与可卡因分离成功并且可作商业性生产;皮下注射医疗之发明;水合氯醛(安眠药用)等合成瘾品之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等半合成衍生物之发现与制造。”
而朱洁这部《长大成人》,所展现给世人的正是改革开放后,有关毒品与中国纠缠的历史之最新一章——中国摇滚音乐挣扎于欲望洞开的丛林时代。
“一首歌明星”的中年危机
日后那些爱恋毒品的明星们估计没看过贾宏声的《昨天》与朱洁的《长大成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细节,但主题没变,叙述单一。
本刊不完全统计了自朱洁、罗琦后若干公开吸毒史或因吸毒被抓的明星,主要是内地明星或在内地吸毒被抓的明星。
至少有24位,其中绝大多数为男性。从案发时间上看,2014年无疑是最高峰,迄今为止已经有9位。2000年前案发或公开的只有前面提到的罗琦、贾宏声与朱洁,2004至2008年3起,2009年之后明显上涨,直逼今年,如2009年满文军等3起,2010年零点乐队大毛二毛等3起,2011年莫少聪、孙兴2起,2012年张默1起(2014年亦有份)。
从职业看,24人中,歌手与演员平分秋色,各占8人、10人,导演4人,鼓手2人;从案发先后看,早年歌手多,越靠近现在演员与导演越多。
但今天回想起来,不少吸毒艺人的前尘往事都已面目模糊。原因在于,这些艺人都不是在事业鼎盛期曝出吸毒新闻的,很多都可归为“中年危机吸毒现象”。
景岗山、谢东、含笑、满文军,均属“一首歌歌手”,他们早年有了成名作之后事业再无突破,进入低潮期。导演张一白、张元的情况类似。张一白在《将爱情进行到底》之后,作品始终无法突破处女作,张元的导演事业也是开头叫好,而后走低。演员莫少聪和孙兴则是成名太早,尝过走红滋味,人到中年后演艺生涯乏善可陈,给观众留下“过气老明星”的印象。
2011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40岁吸毒现象”:“按照艺术规律,40岁以上是创作的成熟期,对作家、导演来讲特别如此。如果一名导演在40岁之后陷入迷茫,就会产生焦躁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当他遇到毒品的诱惑时,就很难抵抗。而对歌手而言,40岁后如果不能实现转型,找到自己的位置,则比导演更容易焦躁。”
如本刊统计的,这一批涉毒艺人多为男性,这也和男性更在意事业发展,承受更多社会压力有关。例如含笑在《飞天》一曲走红后,和妻子一起成立了音乐公司,但因经营不善,音乐公司最终破产,含笑曾在2002年向银行贷款30.08万元用于购买轿车。此后,含笑未能按时还款被银行起诉,心理状态可想而知。
孙兴是在金宝街某饭店的饭局上被抓的。执法过程中孙兴一直面带微笑,称自己因两次婚姻失败用吸毒排解烦恼:“有苦难言,许多悲伤的事情不能让大家看到。”警察在孙兴家中搜查出了多种毒品,最让人震惊的是他家中有配置“开心水”(液体病毒)的原料和全套工具。当警察从孙兴女友的物品中搜查出大量毒品时,孙兴的淡定神色才褪去,说女友没有工作精神空虚,自己“太宠她了”,因此陪她一起吸毒,说到动情处还流泪了。
孙兴重度沉迷毒品的新闻在三年前引发不少联想,港媒一度传说他是被莫少聪供出,而他自己被抓后又供出多位重量级艺人,包括天后级人物。这和现在房祖名、柯震东吸毒事件的舆论气氛非常相似。
当年莫少聪本人不否认自己提供过线报:“他们会通过我的口供去调查当天的人,然后把所有的口供对在一起才会相信我说的话,不是我随便说什么他们就相信。”
如今的明星更像是产业链条上的终端产品:大多速成,也大多速朽,前仆后继,面对着太多的大起大落,毒品,成为其中一些人的避风港,更是黑洞。
圈子
8月份的一多半时间,房祖名远离了北京二环内600多平米、有视网膜识别功能的门禁系统的Naga上院豪宅,取而代之的是六环边城乡结合部的看守所,在那里,人均3平方米,热水澡一周限一次,一次3分钟。而邻居柯震东正穿着不能有鞋带的平底鞋在墙上划“正”字。
对于吸毒而言,此处的豪宅更有一番意味,那是一个圈子,一种身份,甚至被看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吸毒不再仅仅是明星满足自己的毒瘾,似乎也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时尚,一种用来划分是不是“同类”的标准。
在上述本刊对24名吸毒明星的不完全统计中,吸毒地点在家中或朋友家中的有12例,其中明确被报道为聚众吸毒的4例;在酒店吸毒的4例;在酒吧歌厅等演艺场所的2例。除去案发地点最为奇怪的导演张元与景岗山——前者在北京南站涉毒被捕,后者是在首都机场——多人参与是普遍现象。
从媒体报道看,很多明星第一次触碰毒品的经历都与身边朋友有关。例如在含笑因吸毒被捕时,供认自己第一次吸毒是在好友谢东的劝说下尝试的;莫少聪被捕后,也表示自己因推脱不掉“应酬”而吸了两口大麻;当然还有房祖名与柯震东这对“好基友”。
张元被抓时吸的是冰毒,而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电影界知名摄影师、录音师。一位已因吸食冰毒三次被警方抓获的音乐制作人则向媒体分析说,自己第二次吸毒被抓,是像宁财神那样可能被人“点”了,“圈子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我得罪了谁”。
房祖名与柯震东被捕之后,港台媒体一度传闻,这两位年轻明星在狱中供出了一份120位明星的吸毒大名单。虽然这一消息很快被北京警方否认,但娱乐圈内,依然惶惶。
这已经不是贾宏声、罗琦他们吸毒的那个自我放逐的丛林年代了。不但毒品更新换代很快,吸毒者也更看重别人和圈子,甚至形成了一种所谓“亚文化”。
不做“坏小孩”
从今年李代沫吸毒被抓开始,媒体上狼狈亮相的“毒星”不再只是过气明星和中年男子,反而都前景光明,甚至变得越来越年轻。李代沫是“好声音歌手”中辨识度和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宁财神既是知名编剧又是微博大V,柯震东更是当红小鲜肉。
在消费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更年轻,更有钱,也更自我的明星们,与那些前辈相比,身上没有太多包袱。吸毒对他们来说,也被赋予了各种所谓“时尚”意义。甚至有人说,之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请客吸毒。柯震东第一次吸毒是在房祖名家中,可算作“社交吸毒”的一例。曾经的涉毒艺人中,莫少聪委屈地说:“我不是有兴趣吸那些东西,我就想吸一口弄完就可以走了……一大堆人坐那里,你怎么推?”
尤其是K粉、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其社交性更强。北京禁毒教育基地负责人曾说,新兴毒品是一种“俱乐部毒品”,有很强的娱乐性。在制毒行业里,有专门做毒品策划的人,针对艺人的弱点去合成毒品。而娱乐圈内的明星沾染毒品的几率要远远大于平常人。虽然目前并没有明星吸毒占吸毒者比例的大范围统计,但一个小样本调研曾经说这个比例约是5%。
如同当初吸毒行为从摇滚圈扩散到整个娱乐圈一样,明星们的嗜毒癖好,也在向更广的范围蔓延。2008年联合国毒品控制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明星使用可卡因正在鼓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毒。报告首次强调电影演员、体育明星和摇滚歌星在吸毒问题上对意志脆弱的“粉丝”的影响力,并指责警方和法院因“仁慈”对待明星而使情况恶化,没有让吸毒明星成为让人警醒的例子。
中国的数据可以为上述判断提供佐证:根据公安部禁毒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258万人,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的75%。
名利场里的偶像们,很少会注意到这组数据。虽然深陷毒网的明星,并不希望自己的粉丝效仿,但他们也舍不得吸下一口之后出现的梦幻世界。一个化名“假人间”的老娱记写过这样的圈内饭局:“几轮酒汤下肚,就有人从包里拿出了一堆棒棒糖模样的东西,毫不避讳地分发给周围的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没拿,有些人拿来吃了,很快就莫名兴奋了起来,说胡话、高声唱歌、跳舞……这类聚会只有朋友才会被邀请,但类似‘棒棒糖’这样的不明物品,尝试与否全凭个人的意愿,并不强求。但如果跟他们一起‘嗨’,无疑能迅速交到一大帮朋友。”
这种朋友,不啻最佳“损友”。如同瘟疫般的冰毒,就靠着这些“损友”们,在娱乐圈越传越广。
二十世纪初,欧美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说:“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大概是人有吃药的欲望。”但切记,不要吃错药,更要远离毒物。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杭州禁毒
0571-87282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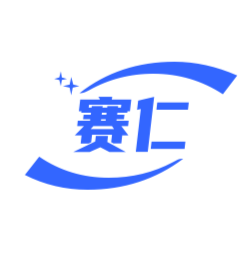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