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名服装名师,在完成“毛装”制作后,搬离中南海,加盟北京东郊民巷“红都服装店”。
“红都”之名,寓意“红色首都”,专为中央首长、来华外国贵宾、外交人员制衣的“红都服装店”,成立于1956年,其主要成员均系当年为“支援首都建设”,从“红帮裁缝”聚居地上海抽调入京的制衣技师。
而“红帮裁缝”,即是宁波裁缝的代称,在上海,服装业以宁波人最众、技术最强、势力最大,而红都服装店的前三任经理也均是宁波人。
可以这么说,新中国初期岁月,中国人的服装门面是由宁波人装点的。
而在淘金逐利的90年代,作为沿海“三来一补”桥头堡之一的宁波,迅速跃为制衣王国,大批纺织服装企业于此崛起,他们以“甬派服装”之名承接了昔日“红帮裁缝”的荣光。
时至今日,14亿人口支撑起了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市场,在这片海量多元、瞬息万变的红海市场,选择了不同道路的宁波纺织服装巨头虽已至中年,但不诉沧桑,行稳致远。
清嘉庆年间,宁波鄞县人张尚义,因出海遇强风浪,只得寄居日本横滨码头靠修补衣物度日。
他趁为外商补衣之机,掌握了裁制西服的要领,逐渐从寄居码头的“难民”,变成裁缝摊老板,最后在东京、神户开设西服店。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宁波人东渡日本学艺。
这则出自1921年版《上海总商会月刊》的故事,是“宁波裁缝”的历史注脚。
作为中国服装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宁波裁缝又称“红帮裁缝”。
他们大多来自宁波奉化江两岸,因吴语中“奉”、“红”同音,加之当时的主要客户是俗称“红毛鬼子”的外国人,“红帮裁缝”由此得名。
“红帮裁缝”发端于日本,却成名于上海。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西方侨民数量大增,与此同时,因中外贸易发展,洋行买办阶级扩大,推动了西服消费群体的形成,社会上出现“西装热”。
于是,大批宁波“红帮裁缝”涌入上海,成为沪上服装业的主角。
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701家西服店中,宁波人开设的有420多家,占比6成以上,从业人员5300人,年产西装10万多套。
而正是这些长期在沪谋生的宁波“红帮裁缝”,成为了日后上海服装产业向宁波转移业务的主要媒介。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乡镇农村办厂热兴起,而服装行业由于进入门槛较低,成为许多镇办/村办企业的第一选择。
便宜的土地与劳动力,加之有缝制衣服的传统,改革初期,宁波鄞州和奉化曾诞生了大量的乡镇服装企业/网络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服装市场的繁荣,大城市中的国营服装企业,却在产能扩张方面存在难度,因此产生了向乡镇服装企业外包加工的需求。
而在上海国营服装店或服装厂中,由于一大批宁波籍“红帮裁缝”的桥梁作用,宁波最终成了上海国营服装店的外包加工基地,而非具备同样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且距离更近的嘉兴、吴江等周边区域。
1984年,雅戈尔集团的前身“青春服装厂”与上海国企开开衬衫厂联营,隔年,青春服装厂业绩翻倍增长,利润超过200万元。
宁波乡镇服装企业通过“红帮师傅”的纽带从上海获取加工业务的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技术支援。
杉杉集团的前身“宁波甬港服装总厂”,在1980年的建厂方案中即表明:“鄞县素称红帮裁缝之乡,盛名于世,生产呢绒服装历史悠久,技术力量有基础。据摸底,县内现有红帮裁缝退休老师傅50人左右,新厂一建立,即可聘为技术辅导人员”。
老一辈从业者的技术支持和业务支撑,让宁波纺织服装基业初创;而此后伴随着创建自主品牌的探索期,以及全球纺织制造业中心迁移的大潮,纺织服装逐渐成了为宁波贡献千亿产值的支柱产业。
1990年,青春服装厂厂长李如成,带着“北仑港”牌衬衫求教北京教授,教授认为这个品牌地域色彩浓,文化含量不够,很难做大。
于是他回到宁波“另起炉灶”,组建新公司,取名“雅戈尔”——YOUNGOR,即原厂名“青春”的英文“YOUNGER”替换了一个字母。
“杉杉”品牌的诞生,则源于甬港服装厂掌舵人郑永刚往窗口的随机一望,院中三棵挺拔的水杉,激发了瞬间的灵感。
拿着借来的3万元,郑永刚也跑到北京,只不过他的目标不是北京研究营销的教授,而是擅于用广告“轰炸”出市场的央视。
广告一出,非同凡响。
90年代,你可能会错过几集《西游记》,却逃不过被央视“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的广告“洗脑”。
杉杉服装品牌史历经三位代言人,“中国的高仓健”翟乃社、“亚洲飞人”刘翔以及“跑男队长”邓超/视觉中国
在那个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年代,宁波纺织服装厂大多以低附加值的低端代工为主,而李如成与郑永刚却选择突破贴牌代工的局限,创建自主品牌,获取溢价空间。
而此时,成立不久的申洲织造所选择的差异化竞争之路,不在于品牌,而是以质量夺取“中高端”代工市场。
创立于1990年的申洲织造,由宁波北仑区政府联合澳大利亚五洲织造有限公司、上海针织二十厂共同投资建立,其取名“申洲”,一是以“申”突出上海特色,二是意把生意做到“五洲”。
三方股东中,北仑区政府负责基建及部分设备购买,上海针织二十厂负责培训和派遣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五洲织造则负责协助选购原料和销售。
曾在日本受训、技术能力过硬的上海针织二十厂技术副厂长马宝兴,作为高级管理人才被引进申洲织造担任副总经理。随马宝兴进入申洲织造的,还有其子马建荣。马建荣13岁辍学做学徒,按其说法,自己是“童工出身”。
至此,马家父子的纺织事业徐徐开幕。
鉴于彼时国内低端代工市场趋于饱和,马宝兴决定切入中高端服装制造领域,并将目光瞄向自己熟悉的日本市场。
当时,日本婴儿服装的利润高,但对质量的要求也更高,甲醛残留、面料质量、色牢度等等指标远超行业标准。为了承接订单,马家父子经历不少周折。当年申洲出产的一批婴儿服装淋水后就掉色,马家父子立即选择烧毁,颇有张瑞敏砸冰箱的神韵。
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为申洲织造带来了稳定的订单,企业渐渐步入正轨。1997年,公司迎来转折点,申洲拿下了它的第一个大客户——优衣库的基本款帝国。
就当申洲织造向服装代工龙头迈进时,“宁波服装业”双雄——雅戈尔和杉杉,正统治着彼时中国商务男装的江湖。
1996年,杉杉全年生产中高档西服35.16万套,销售36.58万套,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5亿元。用郑永刚的话说,“那时做西装,利润率比现在做房地产利润都高。”
1996年,杉杉股份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服装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两年后,雅戈尔登陆上交所,同样拥抱资本市场。
或许是受雅戈尔、杉杉的财富传奇启发,1996年,摆过地摊、开过制衣厂的张江平,决定成立“太平鸟”服装品牌,并与同乡“大佬”们错位竞争,品牌定位中端休闲男装。
但张江平或许没想到,新世纪后,雅戈尔化身“盖房子的裁缝”,杉杉变成锂电材料行业冲浪者,而太平鸟却始终在服装领域坚守。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999年,成立四年的中信证券想要增资改制,公司董事长亲自到宁波找到李如成,希望雅戈尔投资中信证券。
李如成被中信证券的诚意打动,于是雅戈尔斥资3.2亿元,以9.61%的持股比例成为中信证券第二大股东。
这一入股,就是15年。直至2014年,雅戈尔才全部出售所持股份,累计获利近百亿元。
此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下,凭借持有中信证券、宁波银行等公司原始股,雅戈尔获利颇丰;而在房地产疯狂上涨的年代,公司也顺势捞了一把。原来的服装企业,已成为横跨金融、服装和房地产三大行业的综合型集团。
有关雅戈尔“不务正业”的批评,李如成如此回应,“什么主业不主业的,赚钱就是我的主业。”
也是在1999年,郑永刚给正在进行863课题研究的鞍山碳素研究院投资8000万元,以保证课题完成,“随后投资3个亿,在上海浦东建厂做负极材料,开始企业转型。”
涉足与起家产业毫不相关的锂电池业务,曾让郑永刚备受争议。
他曾多次公开解释杉杉转型的原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发觉中国市场将对世界开放,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升级,二是转型。考虑到工厂生产模式、产品设计等实际情况,公司很难升级为类似优衣库、ZARA这类的运作模式,因此毅然决定要转型。”
与雅戈尔、杉杉不约而同走上转型道路,进行多元化布局不同,太平鸟与申洲国际(原申洲织造)选择坚守服装主业,开启升级之路。
创立稍晚的太平鸟,从休闲男装拓展至时尚女装,此后又踏准了“品牌年轻化”、“电商时代”的节奏,吃到时代红利,火了一把。
而申洲国际寻求突破的关键在于,从纯粹的OEM逐步向ODM模式转型。
所谓OEM,即代工企业只专注于生产制造,对于设计、销售等环节“无权过问”。这种模式下,代工企业十分被动,产品附加值低,议价能力低,因此利润自然相当微薄。
而ODM意味着从设计到生产都由代工企业自行完成,产品成型后,品牌方直接贴牌买走。别看只是比OEM多了一个设计环节,但它让代工厂家有了产品的知识产权,由此也形成了一定的话语权,议价能力随之提升。
谈及申洲国际为何没多元化发展,马建荣自谦“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笨’、比较‘土’,只会做纺织”/视觉中国
2005年,申洲国际港股上市,马建荣将融到的9亿港元全部用于设备升级改造,其中有1/4用于升级运动服装面料的研发技术,还扩建了一所6000平方米的面料实验室。
凭借在运动鞋服面料上的研发优势,申洲国际经过严苛的供应商考核,逐步拿下了Nike、Adidas、Puma等头部品牌。
从2005年到2010年,申洲国际销售收入从24.83亿元一路增长至67.19亿元,与此同时,运动鞋服的占比也从9.30%增长到50.20%。
2010年,雅戈尔与杉杉的多元化经营也显现成效。
这一年,杉杉1.21亿元的净利润中,有7成由锂电池材料业务贡献;同期雅戈尔净利润高达26.72亿元,其中服装业务的贡献已不足3成,地产和投资业务的净利润分别达到了6.79、12.45亿元。
也是在这一年,宁波规上纺织服装企业资产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10.1亿元。同期宁波规上纺织服装业产值、利税占全市工业的比例约为10%,成为全市十大支柱产业之一。
2014年,越南福东工业区,一个面积达84万平米的工厂拔地而起。
在这里,申洲国际想要复制一整套和国内基地一样的,从面料到成衣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流程。
在随后的六年里,申洲国际的海外基地产能扩充计划持续推进,截至2020年,越南面料工厂贡献了约5成的面料产能,此外,越南、柬埔寨成衣工厂贡献了近4成的成衣产能。
申洲国际国际化产能布局背后,是纺织服装业向生产要素成本更低地区转移的浪潮。
在经历了四万亿经济刺激后,中国内部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环境治理的困扰。纺织服装业不仅要面对劳动力成本和工业用地价格的上涨,还要面对环保制度下的限产。
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以及他国之间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中国纺织服装业也产生了冲击。
2010-2020的十年间,宁波纺织服装产业艰难维持千亿产值规模。
在纺织服装订单因国外疫情冲击出现回流潮的2020年,宁波全市规上纺织服装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135.9亿元,但相较于10年前1208.9亿元的产值规模,仍旧小幅微跌。
纺织服装产业链外迁趋势难以逆转,宁波制衣巨头们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申洲国际顺应产业外迁的趋势,布局海外基地的同时,凭借“一体化生产”巩固护城河。
集坯布/面料生产、染色、印花整理、裁剪等环节于一体的生产模式,有助于缩短全工序整体生产时间,提升供货效率。一般而言,按照行业惯例,从接单到产品上架往往需要三个月,但申洲国际的平均交货周期仅为45天,备料充足的情况下最快可15天交付。
某种程度上,一体化生产的本质也是一种利润获取的延申,基于此,2020年申洲国际销售额达到230.31亿元,是10年前的3倍有余,同期年度利润也突破了50亿元。
2020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马建荣家族仅次于网易丁磊,排名宁波籍富豪榜第二位。
最晚进入服装赛道的太平鸟,选择在品牌转型上寻求突破,加速向时尚化、年轻化靠拢。
2020春夏纽约时装周,太平鸟品牌秀场/视觉中国
这些年,太平鸟一边纽约时装周办秀,打造“太平青年”品牌IP,一边与可口可乐、迪士尼跨界联名,打造“国际化的中国风”,成功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浪花。
2020年,太平鸟的服装业务收入超过了90亿元,同期线上收入占比提升至30%以上。
而杉杉则渐渐偏离了服装这根主线。
作为宁波纺织服装行业最早的A股上市公司,2020年杉杉股份的核心业务已变为锂离子电池材料业务。而曾经的主业服装业务,已于2018年剥离至港股上市。
2020年,杉杉服装收入已不足9亿元,而10年前,这个数字超过15亿元。
而与杉杉同期开启多元化布局的雅戈尔,随着金融投资与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远去,正试图重回服装主业。
2019年,雅戈尔发布《关于投资战略调整的议案》表示,未来将进一步聚焦服装主业的发展,除战略性投资和继续履行投资承诺外,公司将不再开展非主业领域的财务性股权投资。
回顾过往经历,李如成感慨良多:“尽管一个房地产的项目利润动辄5亿、10亿元,但纺织服装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产业,靠一件件卖衣服赚来的钱更稳健、更长久。”
对于宁波政府而言,自然也希望纺织服装能长久地支撑当地经济的发展。
据《宁波市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21-2025年)》,宁波将从强化创意设计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品牌建设等措施入手,提升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能级,力争到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600亿元。
马建荣曾在会上批驳“纺织行业是夕阳产业,是低门槛行业”的论调:他们根本不了解纺织和服装。
似乎每当人们提起产业升级,与之挂钩的都是以芯片设计、半导体先进制程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
但实际上,产业升级的内涵,更多在于站稳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继而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创新升级。
因而,哪怕是在看起来处于产业鄙视链底端的服装代工领域,其实都有大量高附加值的战略高地。
目前,在宁波制衣王国,共有839家规上纺织服装企业,他们正努力向高端消费品和高增值生产活动转型,不愿被淘汰。
因为在这世间,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
文/搜狐城市翟杨
参考资料
[1]申洲国际、雅戈尔、杉杉、太平鸟各年度财报
[2]神秘“红都”:中央领导人制装特供秘闻,凤凰周刊
[3]中南海裁缝回忆:众多领导人中,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文汇报
[4]红帮裁缝:“国之工匠”的百年传奇,鄞州新闻网
[5]社会关系嵌入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宁波服装业案例研究,地理科学
[6]李如成:青春不老雅戈尔,经济观察报
[7]郑永刚:企业家的天职只有一个,浙商
[8]马建荣:中国服装业首富,南方企业家
[9]成本上升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基于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
[10]拆解申洲国际:“纺织业台积电”的崛起神话,远川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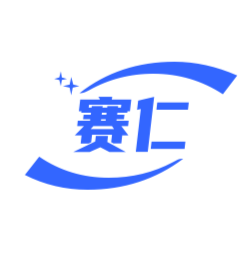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