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海的暴雨下了一天一夜。对于支援张江高科方舱医院的河南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治医师石变和她的同事们而言,每个人都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这个晚上,她们两度冒着职业暴露的危险在雨里狂奔;回家的班车上,用自己的体温将身上的衣服暖干。大雨造成了交接班严重延误,司机也不得不在回程途中一路缓行。当她们终于回到位于松江的酒店时,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05分。此时,大家已有近10个小时滴水未进。
一觉睡醒,石变将这一夜用文字记录了下来。结尾处,她写道,“我们的一生要经历无数个夜晚,或平淡,或幸福,或孤单,这样风雨兼程、勇往直前的夜晚可能是一生的记忆。纵使风雨飘摇,只要内心有光,我们仍然可以迎着东方的第一束光,走出鲜花满径。”
河南援护医疗队至今已在方舱医院度过了16个日夜,方舱里的时光大体上以一种平缓的、波澜不惊的方式流逝。至今尚未有转成重症的患者,医护的主要工作是为患者们开药,进行核酸检测、发放一日三餐,并及时安抚他们的情绪。工作量看似不大,但大家必须克服身着防护服以及通勤带来的种种不便,而个人每天的防护环节也出乎我们意料的繁琐。
石变向晨报记者讲述了自己在这段时期中的日常,那或多或少也是每一名方舱工作者正在经历的。
一线抗疫的关键是感染控制
张江高科方舱医院由10栋楼组成,于4月7日晚交付河南省援沪医疗队管理运行。约1500名来自河南7所大型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进驻方舱,石变来自河南省肿瘤医院,该院此次派出近190名精锐医护人员援护,负责8号楼超过1000名患者。4月16日,第一批80多名患者解除隔离;一天之后,又有100多人获得了出舱证明。但新的患者也在不断进来。
石变和她的同事们是在4月2日这晚接到支援通知的,第二天一早7点,大家就在医院集合了。接受了两小时感控方面的培训,发放一下物资,9点半就往机场去了。他们搭乘下午的航班,两个小时后抵达上海。
石变的先生来送行
石变的先生是同院的医生,来给她送行。两年前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全院也曾经发动医生护士报名,当时她正怀着第二胎,她的先生报了名。但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对于专业要求比较严,因此派去的都是综合性医院呼吸科专业的医生。
石变和她的同事们之前几乎都没有在一线抗疫的经历。去年夏天,郑州起过一阵疫情,她当时只参与过核酸检测工作。无论一名医生有没有一线抗疫经验,感控都是一件不容轻慢对待的事情。所谓的感控,就是感染控制。在方舱医院里,每支医疗队都配备数名感控人员,他们是医疗人员安全以及方舱正常运行的保障。
河南肿瘤医院的医护平时在8号楼工作,4号楼是专门的穿脱区,建立了穿脱防护服的通道,分一脱区和二脱区。正规穿脱防护服是感控的关键点,其中脱的环节更严格。
下班后的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从8号楼前往4号楼,在一脱区进行手部消毒后进入房间。脱防护服的过程中外层的衣服不能接触到内层衣服,脱的时候必须往外卷,接着再脱鞋套和防护面屏。之后进入二脱区,把帽子和口罩脱掉,进行手部消毒,再换上干净的口罩。
在他们进行穿脱时都有感控老师在场,注意检查步骤有没有乱,闭合是不是严,脱的时候有没有沾地上,有没有弄烂等。“现在还装上了监控,要做得不对头上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哪个步骤不对。”
另一个防范要点是回到酒店以后。石变问酒店要了把椅子,进屋前把外套挂在椅子上。外套里面就是手术室里穿的绿色洗手衣,进房间以后先把这套衣服立刻脱掉放脸盆里,泡上消毒液,在上面再盖一个盆。再摘口罩和帽子,这个过程中都要闭着眼睛。“把摘下的东西都放进提前准备的袋子里,扎起来放到屋外。然后赶紧洗澡,冲头发、冲鼻子,这个过程中依然要闭着眼睛。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但不能懈怠,感控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50岁男性患者引起她警觉
4月3日抵达后的这个星期里,医疗队忙着整理方舱设施、准备物资以及进行空舱运行。
“方舱改建得比较急,我们刚到的时候,很多设施和物资还没有准备到位。进去以后,指挥部告诉我们物资药品应该怎么分。开始几天大家就跑上跑下分配物资,做了回搬运工。”
一栋楼四层,每一层就是一个病区。每个病区有二百多个床位,被子和床垫都需要从从一层搬运到各病区现铺,这些工作都由护士完成。空舱运行了三天,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班,一切才算准备齐全。他们还申请了病人需要的诸如卫生纸、湿巾、拉拉裤包括小孩奶粉等必需品,现在都满满当当的备在护士站里头。
4月10日晚上,8号楼开始收治首批患者。“这晚我没有当班,就看到群里消息满天飞。因为一开始上手,难免有些混乱。”石变回忆,“大家在群里此起彼伏地问,怎么给患者发腕带,怎么登记信息,怎么扫码……二楼一共250张床,当晚就收了170多名病人。第二天开始,渐渐恢复了秩序。”
每人一天一个班次,每次4个小时。石变的第一个班次排在4月11日下午4点到晚上8点,当天问诊了大约30多名有症状的患者。“病人一般都会比较焦虑,他们说‘医生,我咳嗽,嗓子疼,我好难受啊!’你给他们测一下心率和指脉氧(在指尖上监测的血氧饱和度),只要氧饱和度大于93,我们就判断这名患者基本上不会转成重症,因为他的肺功能还是很好的。”
所有的病人里有一个却让她心生警觉,这是一名50岁男性,心率达到125次/分钟,而且患者表示自己视力已经模糊,舌头也感到僵硬。
“我一看这病人是有转成重症风险的,就跟指挥部联系。指挥部说要先请专家会诊——整个方舱里面有一个专家团,我就给专家团打电话。他们详细问了这个病人的情况,因为我们方舱里只有基础药物,如果病人肺功能持续减退,是要转运到医院的。我们决定先保持观察。”
1/3时间用来安抚病人情绪
4月12日,石变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察看这名病人,发现“他还是那样,心率还是在110到120之间。”
她立刻向指挥部汇报,坚持这个病人必须转走。“因为我们做医生的,最怕的就是把人家病情给耽误了。”指挥部给出的反馈是已经把情况汇报到定点的周浦医院,但因为院内已没有床位,所以暂时需要等待。
石变向病人了解过疫苗接种的情况,“这名病人之前接种了两针,没有打加强针,的确会存在一点影响。”另外,他本身也非常焦虑,也可能加重了症状。这种焦虑具体表现为不停去办公室找石变,护士也很无奈,“石大夫,这病人又来了。”石变就站到病人床边安抚他,“我说‘你昨天刚进来,现在暂时也没有大碍,再观察一两天。’但说实话,那两天我们医护的心也都是悬着的。”
在方舱的时间里,大约有1/3要花在安抚病人情绪上。“很多病人都会感到焦虑,他们说‘医生,我得尽快好呀!你帮帮我!’‘医生,昨天开的药怎么没用啊,喉咙还是很痛啊,还是会咳嗽呀。’我们就安抚他们,解释这个药具体有什么作用。‘你看你现在氧饱和和心率非常正常,肺功能非常好,你照这样是没可能转成重症的,所以心态放好一点,该吃吃该喝喝,每天测测核酸,说不定哪天就转阴了。”
险情是4月13日这天解除的。“我这天是晚上8点到12点的班,一去接班就去看了那个病人。看到他的氧饱和都到98了,心率也降到80多次了,这下总算放心了。”到4月17日,病人得到了第二份核酸阴性报告,出院在即。
医生在方舱里承担的主要职责是开药,以及判断病人有没有转成重症的可能。石变承认,“这其实不是我们的治疗范围,但是从武汉疫情以来,我们所有的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在培训新冠的治疗措施和防护措施。《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也写得很清楚,看了也就会了。”
实际情况和很多方舱患者描述的不同,这里不只有莲花清瘟。“我们会给患者开一些对症的药物,比如止咳药。对于那些咽喉疼痛比较厉害的患者,则会给他们再加一些消炎药,加一点口服的阿莫西林都是可以的。”
虽然方舱里都是轻症,但很多事也说不准。“前天有个大夫当班的时候,一个30多岁的年轻病人突然就昏迷了,大家当时真是吓得够呛。给他紧急做了心电监护,测了血压、血糖这些。幸好过了十几分钟,病人的意识就恢复了。一直到昨天晚上,大家才把监护撤了。”
打开手机给司机放了首《天路》
4月13日晚到4月14日凌晨,石变经历了人生至今最难忘的一夜。
这天暴雨如注,晚上6点20分,大巴在位于松江的酒店门口将他们接上,1小时10分钟后抵达方舱。因为带进方舱的物品会造成污染,大家都没带伞。身上披上塑料袋,脚上套了塑料袋,等了几分钟没见摆渡车,就钻进雨里往8号楼跑。
“那种感觉真是刻骨铭心,大风疾雨,我生怕把面屏吹掉了,头使劲往里埋,佝偻着身子往前跑,可是外面的隔离衣还是湿了。所幸走了几十米看见了一辆摆渡车,我们站在路中间使劲招手拦住车,坐上了仅剩的两个位置。”
石变在后来的日记里写道。
红色路线是进入方舱的路线,蓝色路线是下班走回来的路线,单程大概需要10分钟
大雨导致大巴晚点,原本应该在14日0点下班的石变和她的同事们一直等到0点45分。出了大楼,依旧是一路拼命奔跑,冒着职业暴露的危险,冲向4号楼。
“大风差点把我的面屏吹掉,口罩已被打湿,我特别紧张,害怕口罩湿后的职业暴露,佝偻着身子一路奔跑,我的头埋在胸前,身子弯成了90度,最外面的隔离衣和鞋子已湿透,终于到了4号楼穿脱区。”
因为交班延迟,最后一名人员直到1点半才上车。回去时依然大雨并无减弱趋势,一路开了1小时40分钟。等一切收拾完看了下表已是04:00,一个班看似4个小时,但从前一晚18:30出发算起,已超过9小时。
下班回程途中的医护人员
“接她们班的这队则由河南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马东阳负责,这队人离开方舱的时候,已是14日早上5点半。“接班是风雨交加的子夜,下班是曙光初现的早晨。我们在公交车上,第二次用体温把自己的衣服暖干。查手机,实时温度14度。我们穿的都是医院发的洗手衣外加一个薄外套,大家饥寒交加,这是一个普通的,上海的早晨。”
马东阳也在朋友圈里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负责接送他们的司机此时也已疲惫至极,他从前一晚10点20分起就不停往返于酒店和方舱之间,此时眼皮已经忍不住在打架。马东阳赶紧走到前排,打开手机给司机放了首韩红的《天路》。
早上7点16分,马东阳的一队医护终于抵达住处,大家和这名司机师傅合了个影,作为对于这趟行程的纪念。
离开10年,上海仍然影响着我
方舱医院的工作量还不算顶大,但医疗队员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由于方舱园区内不建议饮食,而通勤又要花费至少两个小时,很容易饿肚子。最辛苦的是轮到早上4点到8点班次的医护,他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早饭还没送到,而回到酒店已是10点多,这就意味着从前一天晚饭过后有十几个小时是吃不上饭的。
石变胃不好,有一天晚饭把自己塞得过饱,闹起了胃痛。“疼得不行,撑了半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住,就在群里紧急求救。我们后勤老师非常好,立刻给我送来奥美拉挫,喊了快递送达喜,都晚上11点多了还是给送到了。”
这些吃惯了面食的医疗队员来到上海后,出现了水土不服,严重的人甚至开始腹泻。考虑到疫情期间无法现做面条,酒店为大家提供了方便面和馒头。从16日开始,酒店还给每层楼都配了微波炉,下班回来,就可以把饭菜加热一下再吃。
石变这些天最挂念的是自己的一双儿女,她说,“孩子是最大的软肋,现在只要有人和我提孩子,我就想哭了。”她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我家老大是女儿,今年6岁了。4月2日那天和她说,妈妈要去上海支援抗疫,那边的病毒很坏,让很多人都生病住院了,妈妈要去帮助他们。她现在已经懂这些了,幼儿园老师也会给他们画些漫画,教些防疫措施。我女儿一听就哭起来了,说‘妈妈你别走,如果你也生病怎么办?’。”
石变的儿子今年1岁多,方舱里最小的孩子和她儿子差不多大。“我都不忍心看那些孩子。有个12岁的孩子,喉咙疼,嘴巴都张不开,说不上话,我看了特别心疼,都要掉眼泪了。”
还有个和她自己年龄一般大的男病人,“他昨天问我,自己核酸已经两天阴性了,能不能回去,看上去很着急。”石变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有两个小孩,他的太太和大的那个都感染了,马上就要去隔离了。小的那个才1岁多,这几天在家里呕吐腹泻,他说自己得尽快回去照顾孩子。”这名病人已经于4月17日顺利出院,走的时候向石变表示了感谢。“我一看他身份证号,和我是同龄人,就特别能感同身受,上海人这次太不容易了。”
回酒店路上的石变,一身洗手衣已湿透
石变对上海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她曾经在这里呆过三年攻读研究生。前半年是在二军大进行理论学习,后面两年半则在长征医院边临床科室轮转边做研究生课题。她回忆,自己那时候“有空就喜欢去外滩边上走走,最喜欢的公园是人民公园。看着很多人在露天喝咖啡,觉得特别小资。上海的夜景非常美,灯光璀璨的外滩是我永远珍惜的记忆。对了,我还喜欢和同学一起去田子坊买手工饰品。”
这些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但记忆并没有模糊。在她印象里,无论去到哪里,上海街头永远是人头攒动的。
“虽然离开上海10年了,但在这里耳濡目染的那种上海的高效、公平、规范、精致和优雅,足以影响我一生。此后在郑州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依然被上海的城市文化影响着。在工作中,我努力践行着在上海习得的规范、高效、公平,生活中则处处要求自己做个雅致、平和的柔软女性。”
看到如今静默中的上海,让石变心里很难过,“我想尽自己一份力,让它早一些恢复以往的活力。”石变在二军大的很多同学此次也都在方舱抗疫,“有在世博方舱的,有在国际会展中心方舱的,大家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都在一个群里聊。”
“想到大家都在一座城市里,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战斗,哪怕不在一起,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特别有干劲。希望我熟悉的那个魔都赶紧回来!”
后记
4月17日上午,石变当班。这天她打了一百多份解除隔离的证明,从8点上班的时候开始,花了两个多小时。病人们拿到证明以后非常开心,10点多,接他们的车到了。她注意到,“他们走路的样子都和刚进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能看得出,是真的轻松了。”
石变想,他们会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中,并将发现自己的家从未如此美好。她想起了自己在长征医院时住的宿舍,就在乌镇路上。“下班回家要经过一座小桥,环境很美。”她们的宿舍是一幢独立小楼,还有个院子,院子里种着树。“两棵大树之间拉一根绳子,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就在那绳子上晾洗干净的衣服。”阳光洒下来,洗衣粉的香味飘散开,眼前的世界如此干净、宁谧。
她希望疫情早点过去,自己也许有机会回去看看。
(注:派遣医疗队的七所医院分别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向这些医院和援沪的医护人员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新闻晨报·周到APP 记者 沈坤彧
来源: 新闻晨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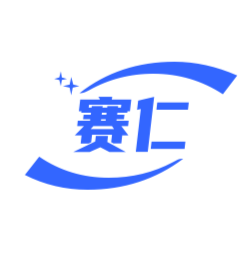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